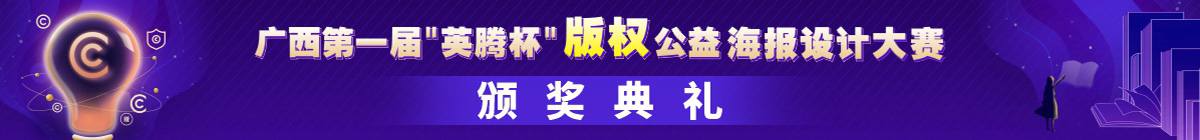作者:张玉颖
第一章 穹窿山的寒雨
公元前517年的深秋,穹窿山的雨已经连绵了半个月。
孙武把最后一块竹简码进藤箱时,指腹被竹篾划出细痕。他抬头望向茅屋外的竹林,雨水顺着青竹的弧度滚落,在泥地上砸出密密麻麻的小坑,像极了他此刻纷乱的心事。
“先生,该动身了。”少年伍子胥掀开草帘走进来,蓑衣上的水珠在泥地上洇出深色的圈。他刚满十六岁,眉眼间却已有了父兄那般锋利的棱角——只是此刻,那棱角被焦虑磨得有些发钝。
孙武将藤箱推到墙角,转身从灶台上拎起半块冷掉的麦饼。“再等两个时辰,”他咬了一口饼,粗粝的麸皮刮得喉咙发紧,“雨势减小些,山下的渡口才会有船。”
伍子胥的手指绞着蓑衣的系带。三天前,他从楚国逃到吴国时,背后还跟着三十名追兵。若不是在穹窿山被这位隐居的齐人所救,此刻恐怕早已身首异处。可他实在等不及了——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的尸身还悬在楚都的城门上,那些乌鸦啄食骨肉的声音,夜夜都在他梦里聒噪。
“先生可知,”少年的声音带着哭腔,却强撑着挺直脊背,“楚平王已经下令,要将伍氏全族的坟茔掘开鞭尸。”
孙武沉默着走到窗边。雨幕中的山峦像一头伏卧的巨兽,雾气从它的脊背上升腾,模糊了天与地的界限。他想起二十年前,父亲孙凭在临淄的宫殿里,也是这样望着窗外的雨,说田氏与鲍氏的争斗,终将让齐国血流成河。那时他才七岁,抱着祖父孙膑传下的兵法竹简,不懂为何父亲要将他送到这千里之外的吴国深山。
“你可知兵者为何物?”孙武忽然开口,声音被雨声泡得有些发沉。
伍子胥猛地抬头:“是复仇的利刃!”
“错了。”孙武摇头,指节叩着窗棂,“是权衡的秤。”他转身从藤箱底层抽出一卷泛黄的帛书,上面用朱砂写着两个字:“吴问”。“三年前,吴王僚派公子光伐楚,我曾问过军中的老兵,为何吴国屡战屡败。你猜他们怎么说?”
伍子胥抿紧嘴唇。他在逃亡路上见过太多吴楚边境的尸骨,那些插着断戟的坟堆,一半在楚地,一半在吴土。
“他们说,”孙武展开帛书,雨水从屋檐漏下,打湿了边角的字迹,“吴人好斗,却不知为何而斗。楚人畏战,却懂得为谁而守。”他忽然将帛书塞进伍子胥怀里,“你要复仇,需先明白,你挥出去的每一剑,究竟要斩向何处。”
少年捧着帛书的手在颤抖。帛书上记载着孙武对各国军制的考察:晋国六卿的田亩制度,楚国的县邑军备,齐国的士大夫私兵……那些枯燥的数字背后,藏着比仇恨更庞大的东西。
雨势渐小时,孙武背起藤箱,伍子胥提着装水的陶罐,两人沿着泥泞的山道往下走。路过一片松林时,伍子胥忽然停住脚步——林间空地上,散落着数十支箭簇,箭杆上还留着楚国军队的烙印。
“是三天前追我的那些人。”他压低声音,手按在腰间的短剑上。
孙武却蹲下身,捡起一支折断的箭。箭头的倒钩上还挂着一丝布条,是齐地特有的靛蓝色。“不是你的追兵。”他指尖抚过箭杆上的刻痕,那是齐国临淄兵器坊的标记,“是冲着我来的。”
伍子胥愣住了。他一直以为这位隐居的齐人只是个普通的避世者,可那些刻着齐国标记的箭簇,像突然从水里冒出的礁石,撞碎了他所有的猜想。
“先生究竟是谁?”
孙武站起身,将箭簇扔进草丛。“二十年前,齐国人叫我孙长卿。”他望着山下渐渐清晰的河流,“现在,我只是个想看看吴国战场的过客。”
渡口的老艄公正坐在船头补渔网,看见孙武时,浑浊的眼睛亮了亮。“孙先生,”他放下针线,露出缺了两颗牙的笑容,“您要的东西,我给您收着呢。”
老艄公从船舱里拖出一个沉重的木箱,打开时,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七十二片龟甲。孙武伸手抚摸那些布满裂纹的甲片,龟甲的冰凉透过指尖传来,像极了祖父孙膑在马陵道大败庞涓时,随身携带的那副占卜甲。
“这些年辛苦您了。”孙武从怀里摸出一块玉佩,那是和田玉的质地,上面刻着简化的“孙”字。
老艄公却摆手:“当年若不是您父亲救了我儿子,我这把老骨头早喂了鱼。”他忽然压低声音,“昨晚有艘船停在对岸,船上的人带着齐国的令牌,问起过您的去向。”
伍子胥的手又按在了剑柄上。孙武却只是淡淡一笑,将龟甲箱搬上船:“告诉他们,我去姑苏城了。”
船桨划破水面时,伍子胥终于忍不住问:“那些龟甲是用来占卜的吗?”
“是用来记东西的。”孙武从怀里掏出一支青铜刀,在龟甲的背面刻下“兵者,诡道也”六个字。刀锋划过甲片的声音,在雨后天晴的寂静里,显得格外清晰。“有些道理,竹简记不住,笔墨写不清,得用这千年不朽的龟甲才行。”
远处的姑苏城渐渐露出轮廓,城墙在夕阳下泛着青灰色的光。伍子胥望着那座陌生的城郭,忽然想起孙武在帛书上写的话:“强国之军,不在甲胄之坚,而在民心之向。”他低头看向怀里的“吴问”,那些关于田亩、赋税、军备的数字,忽然活了过来,在眼前铺成一条通往楚都的路。
而孙武正凝视着水面上破碎的夕阳。他知道,那些从齐国追来的人,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当年祖父孙膑在魏国受膑刑,父亲孙凭被迫交出兵权,田氏家族步步紧逼,他们将孙家人视为眼中钉——只因那本由姜子牙传下,经孙膑增补的兵法,藏着足以颠覆天下的力量。
船靠岸时,暮色已浓。伍子胥提着龟甲箱走在前面,忽然回头问:“先生的兵法,何时才能写完?”
孙武望着远处姑苏城的灯火,那些零星的光点在暮色中闪烁,像极了战场上尚未熄灭的烽火。“等我看懂了这吴国的山水,”他轻声说,“自然就写完了。”
夜风从河面吹来,带着水汽的凉意。伍子胥忽然觉得,自己背上的不仅是复仇的火焰,还有一个比火焰更沉重的秘密。而那个捧着龟甲的齐人,他的眼睛里藏着一片海,海里既有千军万马,也有万家灯火。
第二章 姑苏城的暗流
姑苏城的城门在卯时初刻打开时,孙武正站在护城河的吊桥上。晨雾还没散尽,守城的士兵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他身上的粗布褐衣,却在看到伍子胥腰间的吴国王室令牌时,立刻换上了谄媚的笑。
“原来是伍公子的客人,”小吏弓着腰接过令牌,指尖在上面的“伍”字上摩挲片刻,“太宰嚭大人昨晚还派人来问起您的下落呢。”
伍子胥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他认得这个小吏——三天前在楚吴边境,就是这人收了楚兵的贿赂,差点把他交给追兵。此刻那谄媚的笑容,像涂在脸上的泥,让人看了作呕。
“不必通报了。”伍子胥把令牌揣回怀里,声音冷得像淬了冰,“我们直接去公子光的府邸。”
孙武注意到,小吏听到“公子光”三个字时,眼角的肌肉跳了一下。他不动声色地跟上伍子胥的脚步,目光扫过城门内侧的墙垣——那里新刷了一层白灰,掩盖着不久前泼洒的血迹。墙角的青苔里,还嵌着几缕黑色的头发。
“昨晚城里出事了?”孙武低声问。
伍子胥点头,手指攥得发白:“公子光和吴王僚又起了争执。据说僚想派他的儿子庆忌攻打越国,光不同意,两人在朝堂上动了剑。”
孙武停下脚步,望着街对面酒肆的幌子。那幌子上画着一柄剑,剑穗却是齐国的样式。“看来,我们来得正是时候。”他微微一笑,迈步走进酒肆。
酒肆里只有一个客人,背对着门坐在角落,手里把玩着一枚青铜虎符。听到脚步声,那人缓缓转头,露出一张布满刀疤的脸。“孙先生,别来无恙?”他的声音沙哑,像是被火烫过的铁皮。
孙武的手按在腰间的匕首上。这人是田氏的家臣田单,三年前在齐国追杀过他的兄长。此刻对方穿着吴兵的铠甲,虎符上的“田”字却暴露了身份。
“托你的福,”孙武拉过一张木凳坐下,“还能喝上吴国的酒。”
田单将虎符拍在桌上,酒液溅出杯沿。“家主说了,只要你交出兵法,临淄的宅子还给你,孙氏族长的位置也给你留着。”他的刀疤在晨光里泛着红,“否则,你弟弟在齐国的日子,不会好过。”
孙武端起酒碗,看着碗里浑浊的酒液。他想起弟弟孙谋,那个总爱抱着竹简跟在他身后的孩子,今年该满十五岁了。父亲去世前,特意将弟弟送到莒国避难,可田氏的势力早已渗透到那里。
“兵法我已经烧了。”孙武喝了口酒,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,“不信,你可以去穹窿山搜。”
田单冷笑一声,从怀里掏出一卷帛书,正是孙武留在茅屋里的《兵势》篇。“这是什么?”他将帛书扔到孙武面前,“家主说了,你若执迷不悟,明年今日,就是你弟弟的忌日。”
伍子胥猛地站起身,手按在剑柄上。酒肆老板吓得钻到柜台底下,几个跑堂的伙计早就溜得没影了。
孙武却慢悠悠地捡起帛书,用指尖抚平褶皱。“这只是我写给自己看的杂记,”他将帛书凑到烛火边,火苗舔舐着边缘,“既然田先生这么喜欢,就拿去吧。”
田单的刀疤脸瞬间扭曲。眼看着帛书被火焰吞噬,他猛地抽出腰间的剑:“敬酒不吃吃罚酒!”
剑光闪过的瞬间,孙武侧身躲过,顺手将桌上的酒壶砸向对方。田单挥剑劈开酒壶,酒水混着陶片飞溅,却不知孙武何时已绕到他身后,手肘重重撞在他的后心。
“咳——”田单喷出一口血,剑哐当落地。他难以置信地回头,却看到孙武捡起地上的虎符,轻轻一掰,那青铜铸就的符牌竟应声而断。
“告诉田乞,”孙武将断符扔到田单脸上,“想要兵法,就自己来取。”
田单挣扎着爬起来,恶狠狠地瞪着孙武:“你会后悔的!”他踉跄着冲出酒肆,腰间的伤口还在渗血。
伍子胥看着田单的背影消失在街角,才松了口气。“先生为何不杀了他?”
“杀了一个田单,会来更多田氏的人。”孙武将半截虎符揣进怀里,“而且,我需要他把消息带回齐国。”
酒肆老板颤巍巍地探出头:“客官,这账……”
孙武放下一串刀币,拉起伍子胥往外走。“去公子光的府邸。”他的脚步轻快,仿佛刚才的打斗只是掸掉了衣袖上的灰尘。
公子光的府邸在城东北角,院墙比别处高了三尺,门口的石狮子嘴里叼着青铜环,环上刻着“兵”字。守门的侍卫看到伍子胥,立刻通报进去,显然两人早有往来。
穿过三重院落,孙武在书房见到了公子光。这位吴王僚的堂兄正趴在案几上看地图,听到脚步声,抬头露出一双鹰隼般的眼睛。他的左手缠着白布,渗出暗红的血迹——想必是昨天朝堂上争斗的痕迹。
“孙先生,”公子光起身行礼,动作却不卑不亢,“伍胥多次向我提起您,今日得见,幸甚。”
孙武回礼时,注意到案几上的地图。那上面用朱砂标注着吴楚边境的城邑,其中居巢、钟离两地被圈了红圈,旁边写着“水战”二字。
“听说先生对兵法颇有研究?”公子光请他们坐下,侍女端来的茶水里飘着几片茱萸,是齐国的风俗,“不知先生如何看待吴楚之战?”
孙武端起茶杯,热气模糊了视线。“吴国若想胜楚,需先明白三件事。”他伸出三根手指,“其一,楚地多水泽,战车无用,需练舟师;其二,楚人崇尚巫鬼,可利用其祭祀之时突袭;其三,”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公子光缠着绷带的手上,“吴国内部若不统一,纵有百万雄师,亦是枉然。”
公子光的手指猛地攥紧茶杯。吴王僚即位后,一直想削弱公子光的兵权,这次派庆忌攻越,就是想扶持自己的势力。朝堂上的明争暗斗,早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
“先生可有破解之法?”公子光的声音压得很低,茶盏在他手中微微颤抖。
孙武从怀里掏出那半截虎符,放在案几上。“齐人田单就在城中,他是来杀我的。”他看着公子光的眼睛,“若您能帮我除掉他,我便帮您训练一支可以破楚的军队。”
公子光盯着那半截虎符,忽然笑了。“先生可知,田氏在吴国也有眼线?”他起身走到地图前,用手指点着吴都姑苏的位置,“三天前,田单就住进了太宰嚭的府邸。”
伍子胥猛地拍案:“嚭那个奸贼!我早就觉得他和楚国人有勾结!”
孙武却陷入沉思。太宰嚭是楚国人,父亲被楚平王所杀,才逃到吴国做官。按说他该和伍子胥一样痛恨楚国,可为何会窝藏田氏的人?这里面的关系,像一团缠在一起的麻线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“今晚,太宰府会有一场宴会,”公子光忽然说,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,“庆忌会亲自出席。若先生敢去,或许能找到答案。”
孙武看着窗外的石榴树。昨夜的雨打落了不少叶子,露出藏在枝叶间的鸟巢。一只雌鸟正衔着虫子飞回来,巢里的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,声音里满是对食物的渴望。
“我会去的。”孙武站起身,将那卷被田单扔还的《兵势》篇放在案几上,“这是我送给公子的见面礼。”
公子光展开帛书,看到“凡战者,以正合,以奇胜”时,眼睛骤然发亮。伍子胥凑过去看,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阵法:雁行阵如何破长蛇阵,鱼鳞阵如何抵御骑兵,连夜间劫营时火把的数量都有讲究。
“先生真乃神人!”公子光抚着帛书,指腹在“奇正相生”四个字上反复摩挲。
孙武却只是淡淡一笑:“这不过是前人的经验罢了。真正的兵法,藏在人心和土地里。”
离开公子府时,夕阳正斜照在街道两旁的酒旗上。伍子胥忽然问:“先生真的要去太宰府?嚭那个人阴险得很,说不定是个陷阱。”
孙武抬头望向城墙的垛口。那里有个黑影一闪而过,穿着吴兵的铠甲,腰间却挂着齐国的玉佩。“就算是陷阱,”他轻声说,“有些门,也必须闯进去。”
夜色降临时,太宰府的灯火亮如白昼。孙武穿着伍子胥借来的锦袍,混在送礼的宾客中走进大门。庭院里的戏台正演着《采薇》,乐师们弹着楚国的瑟,歌女们唱的却是齐国的调子——这太宰嚭,果然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。
他在人群中看到了田单,对方正和一个穿着吴国王室服饰的年轻人说话。那年轻人身材高大,腰间佩着一柄长剑,剑鞘上镶嵌着七颗宝石——正是吴王僚的儿子庆忌。
“听说田先生带来了齐国的好东西?”庆忌的声音洪亮,震得旁边的铜钟嗡嗡作响,“可否让本公子开开眼?”
田单谄媚地笑着,从怀里掏出一个木盒。打开时,里面竟是一卷竹简,上面刻着“孙子兵法”四个字。“这是家主从孙武的兄长那里得来的,”田单压低声音,“据说能让军队百战百胜。”
孙武的心猛地一沉。兄长孙驰早已在三年前的战乱中死去,何来的兵法?这分明是田氏伪造的陷阱。
庆忌接过竹简,翻了几页,忽然大笑起来:“这种小儿科的东西,也配叫兵法?”他将竹简扔在地上,一脚踩碎,“本公子明天就带兵踏平越国,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用兵!”
田单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,仿佛那被踩碎的不是竹简,而是他的魂魄。他慌忙去捡那些散落的竹片,指尖被锋利的断茬划破也浑然不觉。庆忌却已转身走向戏台,腰间的宝石剑鞘在灯火下晃出刺目的光,像极了当年齐景公用来炫耀的那柄镇国之剑。
孙武悄然退到廊柱后,目光扫过庭院角落里的阴影。那里站着两个黑衣人,手里握着短弩,箭镞正对着田单的后心——显然是公子光派来的人。他忽然想起伍子胥说过,庆忌力能扛鼎,却最恨被人当作棋子,田单想用假兵法讨好他,无异于自寻死路。
“孙先生怎么躲在这里?”一个娇媚的声音自身后响起。孙武回头,见是太宰嚭的侍女,手里端着托盘,上面放着一壶酒两只爵。那侍女眼波流转,鬓角斜插着一朵齐国的紫菀花,“太宰说,有位从穹窿山来的贵客,想必就是先生吧?”
孙武接过酒爵,指尖触到冰凉的铜器,忽然明白这侍女的指甲缝里藏着墨痕——她方才定是在誊抄什么文书。“太宰府的酒,果然不同凡响。”他浅饮一口,酒液竟带着穹窿山特有的松针香,“看来太宰对山野之人的口味,倒是了如指掌。”
侍女掩唇轻笑,笑声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:“先生有所不知,三年前小女曾在穹窿山采药,蒙一位齐人先生赠过一本草药图谱。”她凑近半步,声音压得极低,“今夜三更,城西的破庙,有人要见您。”
话音未落,戏台那边忽然传来瓷器碎裂的脆响。庆忌正揪着一个乐师的衣领,将瑟砸在对方脸上:“楚人的瑟也配在本公子面前弹?”鲜血顺着乐师的额头流下,染红了他胸前的楚式绣纹。
孙武趁机将酒爵放在廊柱上,低声问:“是谁要见我?”
侍女的目光瞟向田单,那被庆忌羞辱的齐人正缩在角落,像条挨了打的狗。“是能救您弟弟的人。”她丢下这句话,转身提着空托盘匆匆离去,紫菀花的香气却在孙武鼻尖萦绕不去。
破庙、弟弟、田单……这三者像三颗被线串起的珠子,在孙武脑中连成一个诡异的圈。他忽然注意到,那侍女离去的方向,正是太宰嚭的书房。窗纸上映出两个人影,一个坐着,一个站着,坐着的人手里把玩着一枚龟甲,龟甲的裂纹在灯火下像张张开的网。
“先生认识那侍女?”伍子胥不知何时出现在身边,手里攥着半截断剑——想来是刚解决了盯梢的暗卫。他顺着孙武的目光看向书房,“嚭那老狐狸定在密谋什么,要不要闯进去?”
孙武摇头,指了指庭院中央的铜鹤。那鹤嘴里衔着的青铜球正在转动,球面上刻着的“田”字随着转动时隐时现。“再等等。”他轻声说,“有人比我们更急着掀翻这张桌子。”
果然,三更的梆子刚敲过第一响,田单就像只偷油的耗子溜出了太宰府。孙武与伍子胥远远跟着,见他七拐八绕地钻进城西那座破庙。庙里的香案上点着三支残烛,烛火前跪着个穿粗布麻衣的少年,背影竟与记忆中的弟弟有七分相似。
“谋儿?”田单的声音带着哭腔,从怀里掏出个布包,“快拿着这个,去莒国找田氏的商号,他们会送你去齐国。”
少年抬起头,露出一张与孙谋截然不同的脸,却有着同样清澈的眼睛。“田先生,”他接过布包,里面的竹简硌得手心发疼,“孙武真的会来吗?”
田单还没来得及回答,庙门忽然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孙武背着手站在月光里,手里把玩着那枚刻着“兵者诡道”的龟甲:“我弟弟的字迹,比你仿得好看十倍。”
田单猛地拔剑,却被伍子胥掷来的断剑钉穿了手腕。鲜血溅在香案上的残烛上,火苗“噼啪”爆响,照亮了少年怀里布包露出的一角——那竹简上的“兵法”二字,竟是用楚国的朱砂写就。
“是太宰嚭让你这么做的?”孙武步步紧逼,龟甲在掌心转得飞快,“他想借田氏的手除掉我,再嫁祸给公子光,好让庆忌彻底掌控兵权?”
田单疼得浑身发抖,却仍嘴硬:“你弟弟……真的在我们手上!”
“去年冬天,莒国的雪下了三尺厚。”孙武忽然说,声音轻得像雪花落地,“我弟弟在信里说,他养的那只齐国猎犬,学会了捉吴国的鲈鱼。”他蹲下身,看着田单惨白的脸,“田乞派去的人,恐怕连莒国的城门都没进去就冻死了吧?”
田单的瞳孔骤然收缩,像被冰水浇透的炭火。原来孙武早就布好了局,那些关于弟弟的威胁,不过是自导自演的戏码。
伍子胥一脚将田单踹翻在地,剑刃抵住他的咽喉:“说!太宰嚭和楚国人到底有什么交易?”
就在这时,庙外忽然传来马蹄声。庆忌带着亲兵闯了进来,看到眼前的景象,宝石剑鞘“哐当”落地:“好啊,田单!竟敢勾结孙武谋害本公子!”
孙武捡起那卷伪造的兵法,忽然笑了。他将竹简扔到庆忌脚下,上面用楚国朱砂写的字迹在月光下格外醒目:“公子请看,这上面的字,是不是和太宰府书房里的密信一模一样?”
庆忌捡起竹简,又看看田单手腕上的断剑——那分明是公子光麾下侍卫的制式。他忽然明白了什么,一脚踩碎田单的手指:“把这齐贼拖下去,明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,车裂!”
亲兵拖走田单时,那少年早已趁乱溜走。孙武望着他消失的方向,忽然想起侍女鬓角的紫菀花——那是齐地女子用来悼念亡兄的花。
破庙的烛火终于燃尽,天边泛起鱼肚白。伍子胥擦着剑上的血:“先生早就知道庆忌会来?”
“庆忌要攻越,最怕公子光在背后捅刀子。”孙武将龟甲揣回怀里,上面新添的刻痕硌得胸口发疼,“我们不过是帮他递了把刀。”
两人走出破庙时,姑苏城的晨雾正渐渐散去。孙武忽然停下脚步,望着城墙根下卖豆浆的摊子——那老板正在用齐地的法子点卤,手法与父亲当年在临淄教他的分毫不差。
“接下来,该去看看吴国的军队了。”他轻声说,晨光落在他的侧脸,将那些隐忍的纹路照得格外清晰。远处的军营传来号角声,像极了他刻在龟甲上的那些字,正一字一句地,敲打着这个乱世的黎明。
第三章 演武场的血痕
吴国的军营扎在姑苏城东的胥江岸边,连绵的帐篷像一群伏在地上的灰色巨兽。孙武跟着公子光走进营门时,正撞见一队士兵扛着长矛跑过,铠甲的铁片碰撞声里,混着几声越国话的咒骂——这些士兵竟是去年从越国俘虏来的,连吴语都讲不流利。
“这就是吴国的精锐?”孙武停下脚步,望着远处校场上歪歪扭扭的队列。几个士兵正围着酒坛赌钱,骰子声盖过了巡逻队的口令。
公子光的脸色有些难看。“先生有所不知,”他压低声音,“僚即位后,把老兵都派去守边境,留在姑苏的都是些贵族子弟,仗着父兄的权势混日子。”他指向校场中央的高台,“那是庆忌的亲卫营,号称‘天下第一锐士’,你看他们的阵型。”
孙武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,只见高台下的士兵排成方阵,却东倒西歪像堆被风吹过的麦秆。为首的将领搂着两个歌女喝酒,连公子光来了都懒得起身。
“这样的军队,别说伐楚,”孙武捡起地上的半截箭杆,上面的羽毛早就被虫蛀空了,“恐怕连越国的农夫都打不过。”
这话恰好被亲卫营的将领听到。那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,曾在太庙前徒手打死过黑熊,此刻将酒碗往地上一摔:“哪里来的野夫,敢在此妄议吴军?”
孙武没理会他的咆哮,反而对公子光说:“请借我三百士兵,再加一面鼓。”
半个时辰后,校场上的赌徒和醉汉都被驱赶到围观台上。孙武穿着一身素色麻布袍,站在演武场中央,身后立着面牛皮大鼓。三百名被临时抽调的士兵站在他面前,有老有少,有吴人有越人,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楚国降兵。
“你们可知为何而战?”孙武的声音不高,却像石子投进静水,在每个士兵耳边荡开涟漪。
底下一片哗然。一个断了左臂的老兵嗤笑道:“还能为了啥?抢楚国的粮食,睡楚国的女人呗!”
哄笑声里,孙武忽然敲响了鼓。“咚——”的一声,震得围观台的木柱都在颤。“第一通鼓,列阵!”他拔出伍子胥递来的剑,剑尖指向东方,“左列持盾,右列握矛,越人站前排,楚人站后排!”
士兵们你看我我看你,磨蹭了半天才歪歪扭扭地站成三排。那亲卫营将领在台上拍着栏杆大笑:“就这德性,还想演兵法?”
孙武没抬头,又敲响了第二通鼓。“第二通鼓,变阵!”他剑指南方,“前排下蹲,后排上举,盾手护矛手,矛手看盾手!”
这次更乱了。有个越国少年慌得把盾扔在地上,被旁边的楚兵推了个趔趄。围观台上的嘲笑声浪差点掀翻帐篷。
公子光的手心捏出了汗。他看向伍子胥,对方却只是望着孙武的背影,眼神里有种莫名的笃定——就像当年在穹窿山,孙武说“雨会停”时一样。
“第三通鼓!”孙武的剑突然指向西方,鼓声急促如暴雨,“前两排左移,后排右移,形成箕形!”
奇迹发生了。那些刚才还东倒西歪的士兵,竟在鼓声里慢慢挪动脚步。越国少年捡起盾牌护住楚兵的后背,断臂老兵用仅剩的右手举起长矛,连最桀骜的吴人都下意识地跟着身边的人调整位置。当最后一声鼓响落下时,一个勉强算得上箕形的阵形,竟真的在演武场上成型了。
“这阵形有何用?”公子光忍不住问道。
“箕形阵,”孙武收剑入鞘,“可围三面,留一面生路,瓦解敌军斗志。就像捕兽的网,总要留个缺口,才好让猎物自己钻进来。”
话音刚落,那亲卫营将领突然带着十几个护卫冲下高台:“妖言惑众!看本将军撕了你这野夫!”
孙武转身看向冲来的人马,忽然对三百士兵喊道:“想活命的,按方才的阵形列好!”
士兵们愣了愣,竟真的动了起来。前排的越国少年蹲下举盾,后排的楚兵长矛斜指,断臂老兵嘶吼着把身边的人往正确位置推。当亲卫营的人马冲到阵前时,迎接他们的不是散乱的抵抗,而是一片密不透风的盾墙和闪着寒光的矛尖。
“噗嗤——”第一个冲上来的护卫被三支长矛同时刺穿,鲜血溅在越国少年的盾上,那孩子吓得浑身发抖,却死死咬着牙没后退。
亲卫营将领急得红了眼,挥舞长戟劈开两面盾,却被后排的吴人用短刀砍中马腿。战马轰然倒地时,他看见那个断臂老兵正用牙咬着矛杆往前送——原来刚才的嬉笑怒骂里,藏着这些老兵最本能的求生欲。
“停!”公子光突然站起来,声音在混乱中格外清晰,“孙先生,点到为止。”
孙武挥手让士兵退后。演武场上横七竖八躺着亲卫营的人,而那三百临时拼凑的队伍,竟还保持着半个箕形。越国少年的盾牌上全是血,却把下巴扬得老高;楚兵们互相搀扶着,眼里的怯懦少了几分;连断臂老兵都在数自己这队放倒了多少人,嘴角挂着孩子气的得意。
“看到了吗?”孙武对公子光说,“不是他们不行,是没人教他们怎么行。”
这时,一个浑身是泥的传令兵跌跌撞撞跑进营门,手里举着块染血的木牌:“紧急军情!楚军突袭居巢!守将阵亡,粮草被烧!”
公子光脸色骤变。居巢是吴国囤粮的重镇,一旦失守,别说伐楚,连今年的冬天都熬不过去。
“楚军多少人?”孙武突然问道。
传令兵喘着气:“不知道……只看到黑压压的战船,少说有百艘!”
演武场上瞬间安静下来。亲卫营将领瘫在地上,嘴里喃喃着“完了完了”。三百士兵里有人开始发抖,楚国的名号,像座大山压在他们头顶。
孙武却走到那面牛皮大鼓前,手指抚过鼓面的裂痕。“居巢临巢湖,楚军战船虽多,却需逆水而行。”他忽然看向断臂老兵,“你在居巢守过营?”
老兵愣了愣,点头:“守了五年。”
“巢湖有处浅滩,”孙武的声音沉稳如石,“涨潮时能过船,退潮时只能走步兵,对吗?”
老兵眼睛一亮:“对!在北口!叫黑鱼滩!”
孙武提起鼓槌,望向三百士兵。“想不想让楚国人知道,吴国的士兵不是只会抢粮食?”他的目光扫过越国少年的脸,楚兵的手,断臂老兵的独臂,“想不想让家里的婆娘孩子,冬天能吃上饱饭?”
没人回答。但有个吴人悄悄握紧了矛,有个楚兵把盾往身前挪了挪,越国少年的脚往后退了半步——正是箕形阵前排该有的姿势。
“咚——”鼓声再次响起,这次格外响亮,震得胥江的水面都起了波纹。“愿意跟我去居巢的,拿上兵器,跟伍子胥公子走!”孙武的鼓槌指向东方,“公子光,请速调舟师,沿胥江顺流而下,在黑鱼滩西侧接应!”
公子光猛地站起身,腰间的佩剑“呛啷”出鞘:“传令下去!所有能动的船,半个时辰后在码头集合!”
当孙武带着三百士兵走出营门时,那亲卫营将领突然从地上爬起来,瘸着腿追上来:“等等!也算我一个!”他的铠甲还在滴血,眼神却亮得吓人。
队伍路过城墙根时,卖豆浆的齐人老板正往陶罐里装热豆浆。看到孙武,他把陶罐往队伍里一递:“拿着!我儿子当年就是死在居巢,替我看看那里的太阳!”
越国少年接过陶罐,烫得直甩手,却死死抱在怀里。孙武回头望了眼姑苏城,晨光正从城楼的垛口照下来,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,像极了他刻在龟甲上的那些笔画——横是江河,竖是山峦,撇捺是千万个正在起身的士兵。
第四章 巢湖的夜雾
居巢的火光在三十里外就能看见。孙武站在船头,看着那片映红夜空的火光,手里的龟甲被江风冻得冰凉。伍子胥在身后清点人数,除了最初的三百人,又多了七十多个闻讯赶来的老兵,连那个亲卫营将领都带来了二十个护卫。
“先生,”伍子胥的声音带着水汽,“居巢守将是公子光的表兄,据说……尸身被楚军挂在城门上。”
孙武低头看着龟甲上的纹路。那些裂纹像极了巢湖的水道图,有主有次,有曲有直。“楚人越是激怒我们,越说明他们心虚。”他用指甲在一道长裂纹上划了划,“你看这黑鱼滩,退潮时只有丈宽的通道,他们敢把粮草放在那里?”
船行至半夜,江面突然飘起浓雾。伍子胥指挥着船工放慢速度,却听见前方传来隐约的歌声——是楚国人在唱祭祀的调子。
“他们在祭江神。”一个楚兵小声说,“楚人信这个,打仗前必祭神,祭完要喝通宵的酒。”
孙武忽然笑了。他想起在《吴问》里记过的话:“楚俗信巫,每战必卜,卜吉则骄,卜凶则惧。”他转身对士兵们说:“都把火把灭了,船桨用布包起来。”
雾越来越浓,浓得能拧出水。船舷擦过芦苇丛的声音,比楚人的歌声还要清晰。当第一缕微光透过雾霭时,他们终于看到了居巢的城墙——城门上果然挂着几具尸体,被晨风吹得摇晃,像串破败的稻草人。
“先生,直接攻城吗?”亲卫营将领攥着长戟,指节发白。
孙武却指着城外的水道:“看那些芦苇的倒伏方向,水流是往黑鱼滩去的。”他让船工把船藏在芦苇荡里,自己带着断臂老兵和几个熟悉水性的越人,悄悄摸向岸边。
滩涂泥泞得像浆糊,每走一步都要陷下去半尺。断臂老兵忽然停下脚步,指着前方一片发黑的水洼:“那就是黑鱼滩!退潮了!”
雾气中隐约能看见几十艘楚军战船泊在滩涂外,船上的灯笼像鬼火一样晃动。滩涂中央搭着个简陋的祭坛,几个穿着巫祝服饰的人正围着篝火跳舞,旁边散落着十几个酒坛。
“粮草应该在船底。”老兵压低声音,“楚军战船的船腹有暗舱,专门用来藏值钱东西。”
孙武回头打了个手势。芦苇荡里的船开始缓缓移动,三百士兵分成三队,像三条蛇钻进雾里。他自己带着十个人,摸向祭坛——那里的巫祝,正是楚军的软肋。
“天神保佑,此战必胜……”一个白胡子巫祝举着青铜剑,正要往祭台上的牺牲身上刺。孙武突然从雾里冲出,一脚踹翻祭台。青铜剑“哐当”落地,刺穿了旁边的酒坛,醇香的酒液混着鲜血渗进泥里。
“有敌人!”楚军士兵的喊声刚起,就被几声闷响打断——伍子胥带着的人用削尖的芦苇杆,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放哨的卫兵。
混乱中,孙武抓起一把火折子,点燃了散落的酒坛。火舌瞬间窜起,舔舐着雾霭,把楚军战船的影子照得格外清晰。“第一队,占滩涂!”他大喊着挥舞火把,“第二队,烧战船!第三队,接应舟师!”
三百士兵像突然活过来的潮水,涌向各自的目标。越国少年们举着盾冲进楚军阵营,他们从小在水泽里长大,踩在泥泞里比楚兵稳当十倍。断臂老兵用独臂抡着斧头,专砍战船的缆绳,每砍断一根,就大喊一声:“这是替我兄弟砍的!”
亲卫营将领原本还在犹豫,看到一个楚兵举矛刺向越国少年,竟下意识地用身体挡了一下。矛尖刺穿他肩胛骨的瞬间,他反手一刀劈开了楚兵的头颅。“奶奶的,”他啐了口血,“原来打仗不是靠宝石剑鞘!”
当公子光的舟师冲破雾霭时,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:着火的战船在滩涂外挣扎,楚军士兵像被赶鸭子一样往深水区跑,而那支早上还东倒西歪的队伍,正列着个歪歪扭扭的箕形阵,把剩下的楚兵往黑鱼滩的浅水区赶。
“那是……孙武的阵法?”公子光喃喃道。
伍子胥指着阵形的缺口:“先生说,要给楚兵留条生路,他们才会慌不择路地往我们设好的陷阱里钻。”
果然,慌不择路的楚军挤在浅水区,被吴国舟师的箭雨射得像刺猬。有个楚将想往回冲,却被自己人推下水,溅起的水花里混着绝望的咒骂。
太阳升起来时,雾气散了。孙武站在黑鱼滩上,看着满地的楚军尸体和燃烧的战船,忽然弯腰捡起块楚军的盾牌。盾牌背面刻着个“芈”字,是楚国贵族的姓氏。
“这仗,我们赢了。”伍子胥走过来,肩膀上中了一箭,却笑得咧开了嘴。
孙武却摇了摇头,指着那些正在搬运粮草的士兵。越国少年和吴人搭着话,楚兵帮老兵扛着麻袋,连亲卫营的人和断臂老兵都坐在一堆吃干粮——刚才还生死相搏的人,此刻竟像相处了多年的弟兄。
“真正的赢,不是杀了多少人。”孙武把龟甲掏出来,在阳光下看着新添的刻痕,“是让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,知道自己可以为同一件事而战。”
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:“兵法的最高境界,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”那时他不懂,觉得祖父孙膑马陵道杀庞涓才是真本事。可现在看着黑鱼滩上的阳光,看着那些不再互相提防的士兵,他忽然明白了——所谓权衡的秤,秤的从来不是胜负,而是人心。
当队伍带着缴获的粮草返回姑苏时,百姓们在路边摆上了酒和肉。有个楚国妇人抱着孩子,给越兵递了块麦饼;有个吴国老汉拍着楚兵的肩膀,说自己的儿子也在军中。孙武走在人群里,听着各种混杂的方言,忽然觉得刻在龟甲上的字,开始有了温度。
伍子胥凑过来,手里拿着块从楚军将领身上搜来的帛书。“先生你看,”他指着上面的字,“楚平王果然在谋划联合越国,夹攻吴国。”
孙武接过帛书,上面的朱砂字迹和太宰府那卷伪造的兵法如出一辙。他抬头望向姑苏城的方向,太宰嚭的府邸在夕阳下像个蛰伏的影子。
“看来,我们该去见见吴王僚了。”孙武把帛书折好,塞进怀里,“有些账,总该算算了。”
城门口,卖豆浆的齐人老板正等着他们。看到孙武,他咧开缺牙的嘴笑了:“我就知道,先生能让居巢的太阳,照进姑苏城。”他递过来一碗热豆浆,里面飘着几片茱萸,是齐国的味道,却混着吴国的暖意。
孙武接过豆浆,喝了一口。温热的液体流过喉咙时,他忽然想起穹窿山的雨,姑苏城的雾,黑鱼滩的阳光。这些原本不相干的东西,此刻在他心里连成了一片——那或许就是兵法真正该有的样子,既有雷霆万钧,也有润物无声。
终章 竹简上的山河
公元前512年的冬雪,落满了姑苏城的屋顶。孙武坐在穹窿山旧居的窗前,看着最后一片竹简被丝线串起。七十二片龟甲在案头排开,裂纹里的朱砂早已干透,像极了他走过的那些山河——齐地的麦田,吴地的水泽,楚地的山陵。
伍子胥推门进来时,带着一身寒气。他手里捧着个锦盒,里面是吴王阖闾(公子光弑僚后即位)亲赐的剑,剑鞘上刻着“兵圣”二字。
“先生真的要走?”伍子胥的声音有些发涩。这五年,吴国灭了徐国,败了越国,甚至一度攻入楚都郢城,伍子胥终于掘开楚平王的坟茔报了仇。可每次庆功宴上,孙武总是坐在角落,用龟甲记录着什么。
孙武没有抬头,指尖抚过竹简上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“阖闾想争霸中原,”他轻声说,“可这天下,经不起太多征战了。”
他想起去年在郢城,看到楚平王的宫殿被烧成灰烬,百姓们背着孩子逃亡,眼神和当年齐国战乱时的乡亲一模一样。那时他忽然明白,祖父孙膑为何要将兵法藏起来——真正的智慧,从来不该是凶器。
伍子胥打开锦盒,那柄剑在雪光里泛着冷辉。“先生留下的兵法,足够吴国强盛百年了。”他忽然跪下,将剑举过头顶,“子胥替吴地百姓,谢过先生。”
孙武扶起他,将那串竹简塞进他怀里。“这不是兵法,”他笑着摇头,“只是些关于人心和土地的杂记。”他指了指案头的龟甲,“真正重要的东西,都刻在这上面了。”
伍子胥看着那些龟甲,裂纹纵横交错,却隐约能看出“道天地将法”五个字的轮廓。他忽然想起第一次在穹窿山遇到孙武时,对方说“兵者是权衡的秤”——原来这秤上的砝码,从来不是城池与土地,而是万家灯火。
雪停时,孙武背着简单的行囊下了山。老艄公的船还在渡口等着,只是船头的渔网换成了新的。“先生要去哪?”老艄公撑起篙,船缓缓驶离岸边。
孙武望着远处的姑苏城,那里的宫殿依旧宏伟,却比五年前多了些烟火气。“去看看楚国的云梦泽,”他轻声说,“听说那里的春天,芦苇能长到一人高。”
船行至江心,伍子胥带着百姓们在岸边送行。有个越国少年举着当年那面盾,上面的裂痕还在;有个楚兵喊着“先生保重”,口音里混着吴语;卖豆浆的齐人老板挥着手臂,手里还提着个温热的陶罐。
孙武从怀里掏出最后一片龟甲,用青铜刀在上面刻下最后一个字:“和”。刀锋划过的声音很轻,却像一滴水落入江海,在千百年后的时光里,漾开层层涟漪。
许多年后,伍子胥在整理孙武留下的竹简时,发现最末一卷写着: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他忽然想起那个雪天,孙武说“真正的兵法藏在人心和土地里”——原来所谓察,察的从来不是敌我的强弱,而是天地间的生生不息。
而那七十二片龟甲,据说被埋在了穹窿山的竹林深处。每当春雨过后,山民们总能听见泥土里传来细微的声响,像有人在轻轻叩问:这天下,是否安好?